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天津实体经济、金融机构、政府机构该如何做?
- 2019-03-08
- 来源:津滨创新观察
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再次强调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国家对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津考察时深入企业强调振兴实体经济。当前,天津正处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金融“脱虚向实”动力不足,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和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该如何做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个大课题,实体经济、金融机构、政府机构三者又该如何做,值得深思。
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出现的“怪现象”
(一)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旧动能效益下降,新动能强势崛起,看不懂、不适应、理念错位成为金融资源难以流向实体经济的根源
2017年的两会,“脱实向虚”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促进金融机构突出主业、下沉重心,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止“脱实向虚”。但是,当前很多金融产品实际上还是在金融内部来回打转,搞“自我循环”,没有脱离金融这个圈子。2017年9月,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500强中的245家制造业企业,共实现净利润5493.10亿元,占500强净利润总额的19.53%,245家的总利润仅仅相当于6家金融机构利润的一半。
究其根源,当前我国正处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面临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等挑战正在进行转型等原因,旧动能效益确实在下降,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是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10%会保障它在任何地方被使用;20%会使它活泼起来;50%的利润会引起积极的大胆;100%会使人不顾一切人的法律;300%就会使人不顾犯罪,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了。金融作为一类服务业,其逐利的本性驱使金融机构的资源流向利润高的地方。金融机构思维理念仍然停留在工业经济时代,对于强势崛起的新业态、新模式等新动能,金融机构往往看不清、看不明,思维理念的差距导致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对话的“鸿沟”越来越大,这也是企业反映的普遍问题,金融机构远远没有适应新旧动能转换的“新节奏”。
(二)金融资源集聚于国有经济,难以下沉到民营经济,两极割裂现象显著
数据显示我国金融资源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逐年在增多,2018年上半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5548亿元,但是进一步推敲发现,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多集中于国有经济,截至2017年底,央企和省属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负债规模高达99.72 万亿,国有企业的上述负债中大约70%是来自于金融机构的有息负债。反观,以民营经济为主的中小科技型企业,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70%以上的发明专利、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税收,但截至2018年二季度末,在中资行境内贷款中,投向小微企业贷款的占比仅为19.84%。所谓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难”实际上就是“金融服务民营经济难”。尤其,对于近几年突飞猛进的新经济代表,“独角兽”、“瞪羚”企业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仍为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
究其根源,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尚未形成完善的金融定价模式。现行的金融机构运行模式很难下沉到民营企业,如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设计多针对国有企业属性来设计的,包括抵押产品设计、征信模式设计等等,金融机构针对民营企业“软”属性设计的金融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具有轻资产的民营企业在没有抵押担保时,金融机构无法识别其是否是效客户,只能放弃对该类企业的服务。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商业银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是为了惠及民营企业,但从结果来看,商业银行普惠事业部主要是采取引入外部合作机构帮助获取中小企业客户的模式,仍难下沉到民营企业。

二、“新经济”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结合的新方向
新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世界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入新经济时代,是当前最大的时代特征,全球对新经济的讨论和认识不断深入,对新经济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层出不穷。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提出,“世界经济正处在动能转换的换挡期,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发展新经济势在必行”。发展新经济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引领新常态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以瞪羚、独角兽为代表的新经济企业在我国不断涌现,在新的形势下,各地政府也相继出台了瞪羚、独角兽企业培育计划,截止到2018年12月,据不完全统计显示共有16个省、市、县、高新区、工业园区、开发区在企业培育政策体系中涉及到对瞪羚、独角兽企业的培育政策。新经济已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化、释放新动能的核心。
国家高度重视金融服务新经济,加快推进新经济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年6月证监会连发了9个文件,为海外上市的新经济企业将加速回归A股和拟在境外上市的独角兽等创新创业企业境内发新股创造了条件。证监会的举措体现出了资本市场也开始助力国家新经济的发展,探索从金融制度创新的角度来支持我国新经济的发展。总书记在进博会上提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要主动抓住这一轮的新经济红利,近期也出台了科创板的实施细则。对比早期,政府对于“潜在独角兽”、“独角兽”这类企业,缺乏投资眼光、缺乏未来思维,同时基于风险的考虑不敢投资这种创业型企业,错过了互联网时代的红利,百度、腾讯等企业纷纷境外上市。
另外,金融科技能够有效增强传统金融服务对新经济的适应性。去年年底,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北京金融监管局、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出台的《北京市促进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8年-2022年)》(中科园发〔2018〕40号),首次“扶正”了金融科技产业。通过底层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提升金融监管力度。北京、天津、广州等地多联手蚂蚁金服,共同推进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预警防控及金融科技创新发展。早前,由于金融监管的缺位,很多金融机构不敢尝试创新,创新意味着面临前所未知的新型风险,因此很多金融产品的设计仍为制式化的产品,多元化、特色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不到位,金融服务大大降低了对“新经济”企业的适应性,很多新经济发展的红利“局限”在了天使、风投机构的手中。当前,金融科技产业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事中、事后监管能力不断提升,有利于降低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产品创新的风险,增强金融服务对于新经济企业的适应性。

三、实体经济、金融机构、政府机构该如何做
历史上,天津曾是与上海相呼应的北方金融中心,素有“南有上海、北有天津”之称,“港口”外向型经济也促进大量外资资本和外资银行聚集天津。当下,天津如何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做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工作,这需要实体经济、金融机构、政府机构三方携手推进、共同努力。
(一)实体经济:树立“平台思维”,培育新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在2018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曾经提到,“鼓励大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开放创新资源,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IBM的前CEO路易斯·郭士纳说过,“大企业总是不可避免地迟缓而且低效;小企业则灵敏而快速;所以,你应该尽量把大企业拆成一个个的小块。”国内很多实体经济的大企业早就着手进行平台化转型,如海尔的“三化”之一的平台化改革、美的集团的“美创平台”、航天云网等。
工业经济时代,天津依托大工业企业,经济发展领先全国,但是到了当前,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大企业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个体效率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整体效率低下,平台经济将成为一种代表进步的新事物在天津崛起。目前,天津部分大企业已经进行了平台化转型尝试,天士力携手贝壳社打造创新创业平台,提供自身的硬件设施及研发平台资源,是天士力寻求平台化转型的外在布局;九安医疗建设智慧健康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培育孵化出iHealth团队、iSmartAlarm团队、BloomSky团队等。
新经济大环境下,天津大企业进行平台化转型需要做好以下两点,一是提升大企业平台化发展的意识,进行思维的转变,从做事到做局的转变,走向更大的开放包容;二是政府设立引导基金,对大企业平台转型进行补助,帮助企业撮合对接资源,实现精准对接平台化转型所需资源,提升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使其确立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
(二)金融机构:树立“换场思维”,提升服务新经济的意识和能力
当前,企业发展的路径转变了,企业发展求“快”、求“新”、求“变”,若在完成原始的资本累积的基础上再实现进一步发展,产业发展的风口就会“溜走”或被“抢占”,因此在无资本累积的条件下,企业需借力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服务,通过卖股权换取资金、资源网络的支持,完成从“想法”到“创业”脱变,短时间内实现企业的爆发式成长。新经济时代,诞生出了企业发展的新逻辑,而传统金融机构的思维尚停留在工业经济的上半场,企业基于自身的资本累积,完成从“小-中-大-跨国”的线性发展逻辑,助力国有企业、大型企业进一步发展,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但这种玩法只适应上半场,而到了新经济发展的下半场,新经济时代的企业需要的是“雪中送炭”,传统金融机构“脑子”停留在上半场、“身子”却进了下半场的状态是难以在新经济时代得以发展的。
新经济企业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下发展起来的企业,没有靓丽的财务报表、多停留于非盈利阶段,等等,传统金融机构不能用基于对工业经济时代下企业的考核准绳来看待新经济企业,因此,天津传统金融机构要用好“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的牌子、发挥好“自贸区”的制度优势,主动树立“换场思维”,增强服务新经济企业的意识,研发创新符合新经济企业“软属性”的金融信贷产品,打好“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创新监测”组合拳,做好新经济企业的金融供给,助力新经济企业发展。
(三)政府机构:以“新经济服务者”为导向,转变金融政策制定的关注点、出发点
对于天津来说,金融要服务于天津的经济大战略,服务于天津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服务于天津新动能的培育,这应该是一切金融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天津的金融政策要适应这个要求和变化,不能仍然停留在工业经济的发展逻辑里,比如说金融政策要更加支持瞪羚、独角兽等新经济企业。
转变金融政策制定的关注点、出发点,核心是政府要发挥对金融资本的引导作用。一是要进行金融体制机制改革,突破金融对新企业、新模式、新产业投向的限制;二是利用好政府的各类引导基金,做好表率和引导作用,政府引导基金要更多地投向新经济企业;三是用好金融科技,正确引导金融创新。把防控金融风险放首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防控金融风险阻碍金融的创新。所谓的鼓励金融创新,其实就是让更好的、更优质的金融资本、金融机构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点对于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条件下做好金融创新,做好金融监管手段的创新就是一大突破点,现在的金融监管没有过多的运营金融科技的手段,多为被动式监管,金融监管应该要更多拥抱新技术,参照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外经验,加快推进我国“监管沙盒”试点试行,实现金融创新的主动式监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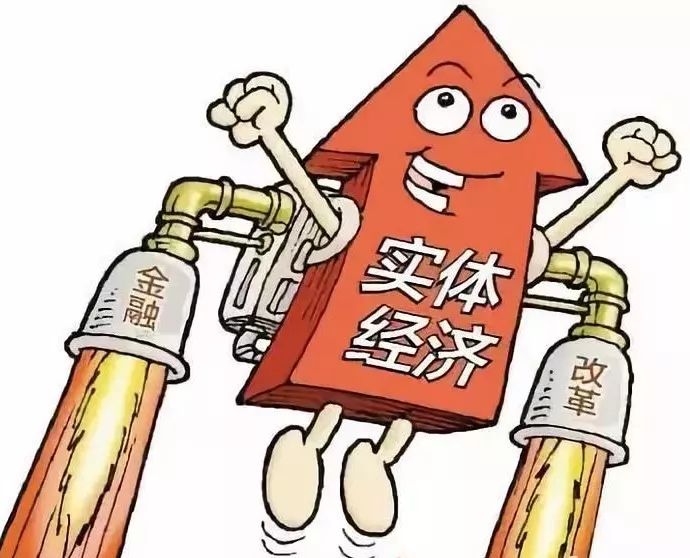
本文版权归长城战略咨询所有,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







合计: {{price}} 元 (不含运费)
去购物车结算